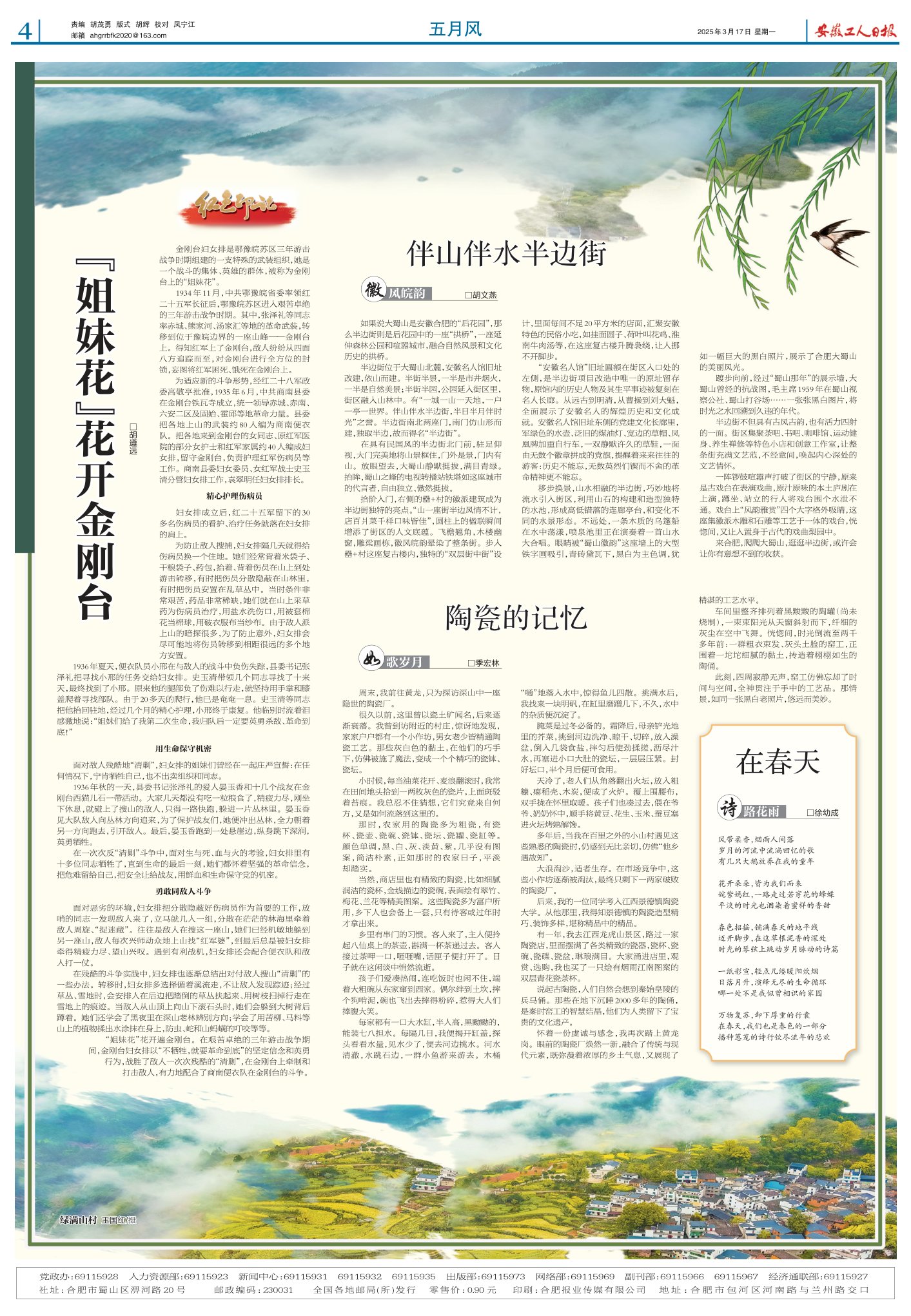周末,我前往黄龙,只为探访深山中一座隐世的陶瓷厂。
很久以前,这里曾以瓷土矿闻名,后来逐渐衰落。我曾到访附近的村庄,惊讶地发现,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小作坊,男女老少皆精通陶瓷工艺。那些灰白色的黏土,在他们的巧手下,仿佛被施了魔法,变成一个个精巧的瓷钵、瓷坛。
小时候,每当油菜花开、麦浪翻滚时,我常在田间地头拾到一两枚灰色的瓷片,上面斑驳着苔痕。我总忍不住猜想,它们究竟来自何方,又是如何流落到这里的。
那 时 ,农 家 用 的 陶 瓷 多 为 粗 瓷 ,有 瓷杯、瓷壶、瓷碗、瓷钵、瓷坛、瓷罐、瓷缸等。颜色单调,黑、白、灰、淡黄、紫,几乎没有图案,简洁朴素,正如那时的农家日子,平淡却踏实。
当然,商店里也有精致的陶瓷,比如细腻润洁的瓷杯,金线描边的瓷碗,表面绘有翠竹、梅花、兰花等精美图案。这些陶瓷多为富户所用,乡下人也会备上一套,只有待客或过年时才拿出来。
乡里有串门的习惯。客人来了,主人便拎起八仙桌上的茶壶,斟满一杯茶递过去。客人接过茶呷一口,咂咂嘴,话匣子便打开了。日子就在这闲谈中悄然流逝。
孩子们爱凑热闹,连吃饭时也闲不住,端着大粗碗从东家窜到西家。偶尔绊到土坎,摔个狗啃泥,碗也飞出去摔得粉碎,惹得大人们捧腹大笑。
每家都有一口大水缸,半人高,黑黝黝的,能装七八担水。每隔几日,我便揭开缸盖,探头看看水量,见水少了,便去河边挑水。河水清澈,水跳石边,一群小鱼游来游去。木桶“嗵”地落入水中,惊得鱼儿四散。挑满水后,我找来一块明矾,在缸里磨蹭几下,不久,水中的杂质便沉淀了。
腌菜是过冬必备的。霜降后,母亲铲光地里的芥菜,挑到河边洗净、晾干、切碎,放入澡盆,倒入几袋食盐,拌匀后使劲揉搓,沥尽汁水,再塞进小口大肚的瓷坛,一层层压紧。封好坛口,半个月后便可食用。
天冷了,老人们从角落翻出火坛,放入粗糠、瘪稻壳、木炭,便成了火炉。覆上围腰布,双手拢在怀里取暖。孩子们也凑过去,偎在爷爷、奶奶怀中,顺手将黄豆、花生、玉米、蚕豆塞进火坛烤熟解馋。
多年后,当我在百里之外的小山村遇见这些熟悉的陶瓷时,仍感到无比亲切,仿佛“他乡遇故知”。
大浪淘沙,适者生存。在市场竞争中,这些小作坊逐渐被淘汰,最终只剩下一两家破败的陶瓷厂。
后来,我的一位同学考入江西景德镇陶瓷大学。从他那里,我得知景德镇的陶瓷造型精巧、装饰多样,堪称精品中的精品。
有一年,我去江西龙虎山景区,路过一家陶瓷店,里面摆满了各类精致的瓷器,瓷杯、瓷碗、瓷碟、瓷盆,琳琅满目。大家涌进店里,观赏、选购,我也买了一只绘有烟雨江南图案的双层青花瓷茶杯。
说起古陶瓷,人们自然会想到秦始皇陵的兵马俑。那些在地下沉睡 2000 多年的陶俑,是秦时窑工的智慧结晶,他们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。
怀着一份虔诚与感念,我再次踏上黄龙岗。眼前的陶瓷厂焕然一新,融合了传统与现代元素,既弥漫着浓厚的乡土气息,又展现了精湛的工艺水平。
车间里整齐排列着黑黢黢的陶罐(尚未烧制),一束束阳光从天窗斜射而下,纤细的灰尘在空中飞舞。恍惚间,时光倒流至两千多年前:一群粗衣束发、灰头土脸的窑工,正围着一坨坨细腻的黏土,抟造着栩栩如生的陶俑。
此刻,四周寂静无声,窑工仿佛忘却了时间与空间,全神贯注于手中的工艺品。那情景,如同一张黑白老照片,悠远而美妙。